
我喜欢农村发的豆腐,更喜欢阿爸阿母发的豆腐,它给我的味道是特别的,随着工作岗位的变换,岁月的变化,已经在漫长的时光中,融入了更多的乡亲、念旧、勤俭、坚忍等情感和信念。
豆腐,是现代人对祖先智慧最好的继承。小时候过节,通山县乡村人家总少不了打桌豆腐来丰盛一下饭桌。阿母做的豆腐特别好吃,细嫩爽滑;豆腐也好看,玲珑剔透,乳白色带点微黄,块块成形有弹性。
黄豆是自家种的,用山泉水浸泡一夜,泡至粒粒膨胀。天蒙蒙亮,阿爸“吱呀吱呀”的推磨声把我吵醒。长长的磨担悬吊在屋梁,阿爸手抓磨把,脚一前一后,身子前躬后仰,周而复始。阿母把泡好的黄豆一瓢一瓢倒入磨眼,配合默契流畅,豆浆延着飞旋的磨合口洒落到老木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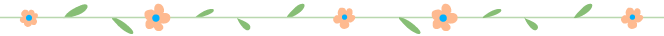
阿母做早饭时由我代劳,阿母教我:“豆子和水要均匀,水多了太稀,水加少了,豆子干磨,拉磨费劲不说,磨出来的豆子粗,浆少,每一瓢水与豆搭配要恰到好处。”磨子在飞快的旋转,要找准磨杆移开的空隙,动作要麻利,慢一点,连水带豆撞飞,我几次连瓢都撞掉了,阿爸只得放慢速度。我最怕阿哥拉磨,有次把磨盘上半边拉跑了,险些砸到我,阿母说他像牛一样只知道低头出悻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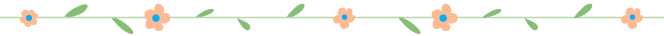


开始滤浆了。茅屋的横梁吊个十字木架,雪白的纱布四角绑在木架的铁环上,阿母把开水冲好的豆浆舀进纱布中过滤。我站在小板凳上,踮着脚双手反复摇晃木架,木架有节奏地荡漾起来,“咔吱咔吱”唱着歌,豆浆顺着纱布流入木桶。越摇纱布里的豆渣越干,阿母双手不停的掐纱包,直揉到像一个面团,再没有浆水出来为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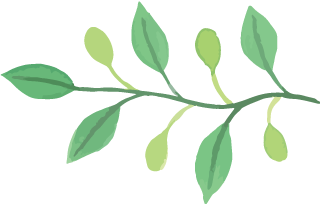
阿母把豆浆烧开,倒入木桶,准备点浆。点浆有讲究,石膏水少了豆腐太嫩,量少;多了、粗了,豆腐太老,不好吃。点浆前,先舀碗豆浆喝了再说,然后扒在桶边,小嘴对着豆浆不停吹风,豆浆的表层起了细细的皱纹,吹得越久,皱纹越深,慢慢形成一层油亮亮的豆油,五个小手指伸开一捏一提,仰头张大嘴巴,豆浆顺着豆油尾端滴到脸上也无妨,长长一串豆油就进入嘴里,软软的,清甜细腻。有时一人吹嫌慢,发动小伙伴一起来吹,大家吹得太专注,口水喷到桶内,鼻涕掉出来也毫无知觉,阿母拿根竹条边赶边说:“看你们的好吃相,都出去玩,待会来喝豆花。”然后长长小竹条伸到豆浆里轻轻一挑,一张圆圆的豆油就挂在了竹条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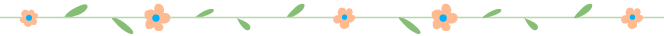
“卤水点豆腐,一物降一物”,一碗卤水或石膏水就能让豆浆发生神奇的变化。我家用的是石膏水点浆,把石膏水倒入豆浆里,搅匀后盖上木盖,过了半个时辰,揭开桶盖,出现大理石一样的花纹,豆腐花就好了。阿母舀两碗让我送给隔壁没有牙的贵凤婆,贵凤婆的傻女儿喝完豆花,手里摇晃着空碗对我“嘿嘿”傻笑不停,意思是还要来一碗。遇到有人从门前路过,阿母定会拉着递上一碗,加点白糖。豆花嫩嫩滑滑,舌尖一触,便轻轻化开,满口生香。你来我往,一碗豆花喝出满满的乡情。吃豆腐的人能安于清贫,而做豆腐的人也懂得“顺其自然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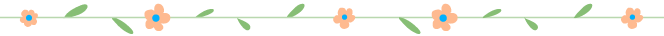
到最后的工序,阿母用一个没底的木盒放在饭桌上,上面盖一块白纱布,我帮忙提着纱布的边角,阿母将豆腐花倒进纱布,上面加压挤出积水,待豆腐渐渐成形,把纱布卷覆在豆腐上,上面盖块木板,阿爸搬几块大石头砸在板上。喜欢吃老豆腐,时间就压久一点,喜欢吃嫩豆腐,时间就压短一点。要是炸成油干吃,用嫩一点的豆腐炸会更泡些。待到豆腐做成后,阿母会把豆渣做成一个个碗口大的豆渣球放在菜篮里,盖上稻草,待长了白须就成了霉豆渣,切成片放在火锅里炖干辣椒特别美味,闻起来香香的,每回都馋得阿爸口水直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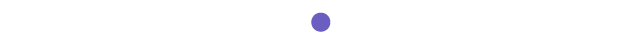
过年的时候,家家户户都会打豆腐、炸油干。炸油干的时候特别香,茅屋顶渗出浓浓的香气在小村庄弥散开来,馨香醉人。阿母炸油干时,我围着灶前转来钻去,只要阿母捞出,抓一把就跑,拿出去分给同伴。刚炸出来的油干,香香脆脆,还有一股清甜。炸好后散一点盐巴,用竹签穿在一起吊在屋梁下,风干后可吃许久。村口的阿公就喜欢吃发霉的油干,阿爸则喜欢油干中心带有绿点,硬邦邦的,有嚼劲。


特别是冬天,全家人围坐在火炉旁,豆腐在吊锅里 “咕噜咕噜”的颤动,甜甜的汤汁充盈豆腐每个蜂窝孔,暖融融的水蒸气氤氲整个茅屋,我们吃着滚烫的豆腐,暖透全身。
据说“腐”“福”谐音,多福长寿的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民间肥沃的土壤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水对豆腐的塑造证明水能滋养人的灵性和觉悟。家乡的豆腐白净濡润,吃后总是意犹未尽,家乡的人如豆腐质朴温厚,那浓浓的亲情乡情,让我魂牵梦绕,一生难忘,让我分不清哪是滋味,哪是情怀。



编后语:文艺也好,文学也好,都与文化有关,她天生好似一朵赏心悦目的白云,在九宫山麓富水河畔轻盈飘逸着,工作、创作,持家,交往,率真,幽默,是那样可爱,又是那样有趣。比如因工作联系的一餐私宴,当时我在外省休年假,硬是等了20天,感动的是我不是哪桌餐的主客。一个人玩命似的下乡指导文艺节目,大热天中午返城把车开进阴沟里,别人惊魂未定,她还在现场发朋友圈。通山最早的新闻届“三阮”之一的阮绪焕老局长有次和我说,冒想到朱凌云会写作。当然,不只是老阮局一人这样意料之外,但是,市作协可是名媒正取的。天生丽质的歌唱家李玲玉作客央视谈如何走上画画这个行业时,是陪儿子学画画时无意插柳柳成荫的,所以,平日里偶尔交集,我也不必咨询她是从哪兴趣出发业余创作的。作为本地唯一的通山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APP云上通山,其刊登的作品不可能对诺贝尔文学奖负责,接地气的前提是,可读,可信,可亲。一路走来,是我对她的简洁评价。(方雷)

作者:朱凌云,女,汉族,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文化馆馆长,湖北省舞蹈家协会会员,咸宁市作家协会会员。2014年10月至今在《文化通山》连载《童年那些趣事》系列,后多次在《珠海特区报》、《香城都市报》、《九头鸟》、《咸宁周刊》、《通山文艺》、《孝感日报》、《湖北日报》等发表散文。写作之于我,犹鱼之于水,是能让我的心灵浸润其中的快慰,是岁月日渐沉积的精神珠贝。

编 辑:徐 微
编 审:乐有钦
监 制:方 雷
总监制:阮胜利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