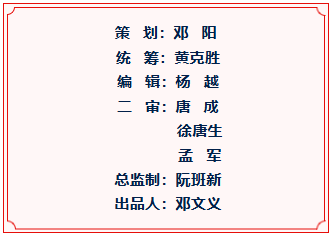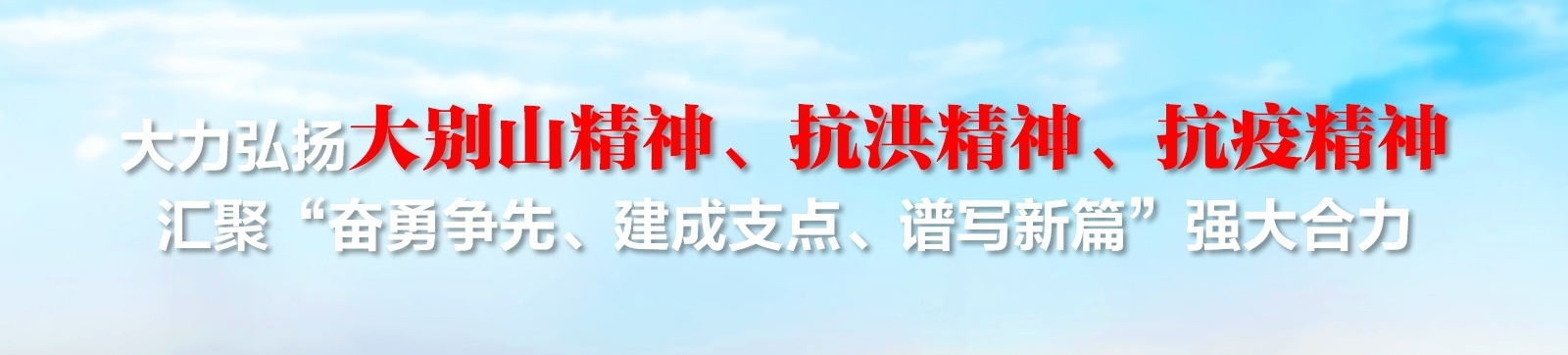《母亲的油渣大白菜》
作者:龙行善
我的老家在两县交界处,是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庄。那里藏着我童年的全部记忆与梦想。乡愁,这两个沉甸甸的字,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同模样。于我而言,乡愁就是母亲炒了一辈子的那盘油渣大白菜——贫寒岁月里,用勤劳与疼爱熬煮出的人间至味。那时乡亲们日子都过得紧巴,能吃饱饭的人家没几个。我家虽不例外,却靠着父母的勤劳节俭与精打细算,从没让我们兄弟几人挨过饿、受过冻。

母亲是离灶台最近的人。家里全年吃的油,大部分都来自“杀年猪”的腌制猪板油。每当母亲炒菜熬猪油时,我总抢着打下手,踮着脚往灶膛里添柴加火。看着一块洁白的板油渐渐缩成金黄诱人的油渣,母亲就用锅铲捞起,夹出一小块吹凉了递给我,轻声叮嘱“慢慢咬”。可我哪等得及,一把抓过塞进嘴里,烫得在舌尖来回翻滚却舍不得吐,折腾半晌咽下,那酥脆的口感、醇厚的香气直沁心脾,整个厨房都飘着勾人的暖意。我记得,母亲是在煤油灯下腌板油,她把板油切成方块,每一块都仔细撒上盐,小心翼翼装进陶瓷坛,用劲按压后撒上盐,然后用尼龙袋覆盖绳子捆绑密封。那罐腌板油,陪着我家熬过了春荒,熬过了夏旱,直到下一个腊月。参加工作后才懂得母亲那句“心急吃不得热豆腐”的道理,才想起母亲当年站在灶台边的模样。原来她哪是在说吃豆腐啊,是把过日子的疼惜都揉进了家常话里。母亲怕我性子急,走得太快摔了跤,悄悄教我:路得一步一步踩稳,就像她煎豆腐那样,慢点儿煎、细心护,日子才能熬出暖滋味,走着走着就宽了,走着走着就踏实了。
母亲是离饭桌最远的人。我趴在灶台边,看她捏着竹筷轻轻在陶罐内夹起一块凝着薄霜般的腊猪油——乳白的脂块刚落进热锅里,热油便“滋啦”一声炸开,瞬间裹住它。不过片刻,脂块融成金黄的油渣子,立刻活泛起来,在水灵灵的翡翠色白菜片间滚跳;油星子沾在菜叶上,把那抹脆绿衬得更亮,连带着暖融融的腊香,也跟着漫满了屋子。铁铲在母亲手中划出温柔的弧线,每片菜叶都裹上薄薄的油光。阳光从糊着报纸的窗棂漏进来,昏暗中,几双饥饿的眼睛亮晶晶的。最后一勺盐撒入锅中,青黄相间的油渣大白菜在煤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。母亲用筷子尖尝了尝,轻声说“好了”,兄弟几个立刻笑着挤到桌边。油渣在筷尖脆响,白菜咬开时的清甜混着猪油特有的荤香,在舌尖绽放成记忆里最奢侈的烟火。这时母亲总倚在厨房门框上,笑眯眯看着我们争抢,冬日暖阳爬上她那布满岁月痕迹的脸庞,那专注于一家生计的模样,温暖了所有寒冬。

小时候总不懂,母亲为何总让我们先吃白菜,后吃油渣。后来才慢慢开悟,这是她教我们的道理:好东西要留到最后,才更懂得珍惜。这朴素的延迟满足里,藏着对生活的敬畏,让我们在美食里学会了耐心与感恩。
母亲走得最多的地方,是菜园。从菜籽落土到嫩芽破土,她总提着旧水桶,吃力地用水瓢给菜苗浇水。八岁那年,我常看见她蹲在菜畦边,一片叶一片叶地打量白菜长势。在她的照料下,白菜从小指粗细长到开枝散叶。母亲常说:“亲戚宜稀不宜密,菜园宜密不宜稀。”亲戚少些虚礼才不添负担,菜园勤照料才长得出好菜。她还说:“勤快勤快,有饭有菜。做人要学白菜,安于平凡,不卑不亢,不用和谁比金贵。”后来读书才知,柳宗元早写下“白菜抱冰雪,黄梁泡醯鱼”的诗句,原来这寻常白菜,早被古人读懂了它的坚韧与风骨。饥荒年代里,菜园里的白菜就是一家人的春色,更是生活的底气。
如今兄弟聚餐,偶尔也炒一盘油渣大白菜,却再也没有母亲炒的味道。或许那味道里,本就藏着母亲的牵挂、岁月的温度,还有再也回不去的时光。母亲离开五年了,但她的勤劳节俭、顽强坚韧,早已成了我们兄弟的底气。那盘油渣大白菜,是乡愁,是记忆,更是母爱赋予我们前行的力量,永远温热在岁月里。
图文来源于网络
朗读者
黄克胜
现供职于通山县融媒体中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