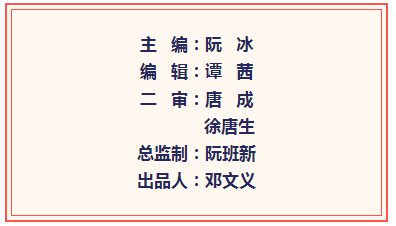仙人塘记
作者:周启兴
“陂塘一曲水泓澄,山簇瑶台十二层。剩脉余膏流不尽,芝田蕙圃岁常登。”宋代陈岩的诗句如一枚古镜,倏然照见黄沙铺镇腹地这一方水土。仙人塘,其名便沾着三分出尘仙气,而待我真切立于其畔,才知此名非虚——山是凝碧的屏障,水是含光的明镜,几户人家点染其间,竟像是从大地深处悄然生长出来的。
群山确如诗中所言“簇瑶台”,环抱之姿深具古意。峰峦叠嶂,由近及远,一层深似一层,苍翠直要滴落下来,将小小村落如婴儿般稳稳揽在臂弯。山色并非单调的绿,晨光熹微时是青黛含烟,日头高悬则化作明晃晃的翡翠;待到暮色四合,又凝为墨玉般的沉碧。山势并非一味陡峭,而是起伏有致,犹如仙人衣袂垂落的柔软褶皱。远望山脊,真疑有琼楼玉宇隐于那苍茫云气之间,只是俗眼难窥罢了。
山势至此温柔一陷,便捧出了那泓令陈岩吟咏的“水泓澄”。塘水清极,宛如大地深处睁开的一只明澈眼眸,毫无保留地将整个天空拽入怀中。水面是镜,水底亦是镜——卵石历历可数,浑圆如经千年摩挲的玉籽,静卧于洁白细沙之上;几尾银鳞小鲫悠然游弋,倏忽往来,影子先于身体落在白沙上,伶俐地画出几道墨痕。微风拂过,水面顿生细纹,天光云影顷刻碎作万点流金,跳跃闪烁不定。待风止水静,那碎裂的金箔又悄然弥合,复归完整,仿佛方才的动荡只是造物主不经意间呵出的一口气。
塘水澄澈如许,倒影便成了另一重世界。岸边竹影婆娑,尽数投入水中,随水波轻摇,翠色洇染开去,宛如水底生出了一片流动的翡翠林。最妙是当山岚初起,薄雾贴着水面浮动,那倒影中的竹林便朦胧起来,虚实相生,直叫人疑心踏入便可步入清凉无垢的幻境。偶有飞鸟掠过,翅尖点破水面,倒影中的翠竹便顷刻碎裂,化作万千翡翠屑,在涟漪里闪烁旋舞,许久方能重归旧影。近岸处,几枝斜出的老树虬枝探入水中,其倒影竟比岸上真身更显筋骨嶙峋,似以水为纸,以影为墨,书写着沧桑遒劲的一笔。
塘边几户,青瓦黄墙,墙由厚实黄土夯筑而成,是大地最朴拙的底色。青瓦叠叠,经年累月,已有苍苔悄然攀缘,新绿与陈年的深黛交织,仿佛岁月在瓦楞上绣出的天然锦纹。晴日里,这青瓦黄墙映着碧水,色彩纯净而分明,宛如一幅设色古雅的工笔。屋檐下的阴影里,几簇凤尾蕨从墙根石缝间顽强探出,细叶在微风里轻颤,竟似应和着水塘无声的呼吸。屋舍无言,与环绕的葱茏草木、澄澈塘水浑然一体,仿佛它们并非人力所建,而是与这山水一道,从亘古的寂静中自然凝结而生。
塘水之胜,更在于四时晨昏间变幻不息的面目。晨起,山间岚气氤氲,如乳白轻纱浮于水面,塘水仿佛一块温润青玉,含蓄着尚未醒透的梦。待日轮升高,驱散雾气,水色便转为通透的碧蓝,日光直透水底,将每一颗卵石的纹路都照得清晰无比,恍如神佛掌中观照的琉璃世界。及至黄昏,夕阳熔金,将漫天云霞一股脑倾泻入塘中,水面顿成一块巨大的、燃烧的玛瑙,“余膏流不尽”的诗意在此刻获得了最辉煌的注脚。暮色四合,水面则渐渐沉静如一块深青的砚池,倒映着初升的星子和微明的灯火,幽深难测。若有月夜,则清辉满塘,水面浮光跃金,静影沉璧,四围山影如墨,水月交融,直让人生出“空明”之叹。便是寒冬飞雪,塘水亦不减清冽,雪花无声飘落,遇水即融,唯岸边衰草与远处青瓦托着素白,衬得那一池寒水更显幽深澄净。
我曾坐塘边,看水中倒影——山峦、竹树、屋舍、流云,甚至飞鸟倏忽掠过的痕迹,皆被这方水镜忠实捕捉。倒影的世界如此清晰,却又因水波永恒的晃动而始终处于破碎与重圆的边缘。水面涟漪轻荡,影像便扭曲、模糊、碎裂,散作万千光斑;待水面复平,万物倒影又悄然凝聚成形。这无休止的破碎与弥合,竟暗合了某种天地间的大道:水不执着于留住任何一帧画面,亦不抗拒任何闯入的形影。它只是容纳、映照,而后任其流转变幻。
仙人塘之水,便是这般“流不尽”的灵脉。它映照过宋时陈岩笔下“瑶台”般的山影,也映照着今日青瓦黄墙上的斑驳苔痕。它澄澈如初,静默如初,以其亘古的流动涵养着这一方芝田蕙圃,也涵养着每一个俯身掬水、得以窥见倒影中那个亦真亦幻世界的过客之心。水波深处,倒影明明灭灭,仿佛时间本身在此处变得柔软而透明,最终只余下那泓澄澈,无声诉说着山水的永恒与清澈的深意——人间纵有万般尘扰,此心若能如这一塘清水,映照万物而不滞于物,便是真正的登临了仙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