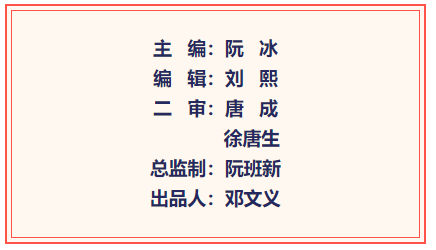花儿冉冉开
作者:朱丽平
边陲小镇,位于省域版图东面,视作湖北的东大门。沙店河、杨林河、洪大源、大洞河贯穿其间,活活泼泼,清亮澄明。每年春夏之交,属地雨量丰沛,洪水漫河,故而称“洪港”。因土壤肥沃,物产丰富,洪港还被称为鱼米之乡。
去洪港那日,头天还阳光明媚的,夜里突然下起雨来,气温骤降十多度。早晨临出发前,雨还没停,负责接待的洪港镇宣委,始终没通知取消行程,背着采写任务的作协文友们,也没谁知寒而退。我穿了厚棉衣,找出棉帽,手套,雨伞,做足了出行准备,依然冷得慌。跳上大巴车,已有文友先到。车顶窗渗水,好几处座位淋湿,无法座人,也没谁埋怨一声。心想,为了让眼睛在天堂,就让身体在地狱吧。
行程首站,是洪港车田村。据车田大族《王氏宗谱》记载,明朝初年,王化寓铸铜车灌溉农田,一时成为洪港奇观。“车田”成了该此地名,也富庶得出了名。车田居洪港西大门,高速伴村而行,国道穿村而过,石英、大理石矿蕴藏量大,草木茂盛,引来好几家企业驻扎,其中两家进入全市规上企业名单库,成为洪港经济的龙头支柱。研发的玻璃产品,满足湖北、安徽、重庆等上市公司市场需求,推动周边省市玻璃产业的快速发展,同时带动就业,物流、五金加工、机械制造等多项产业发展。一家俱厂生产的实木家俱,远销京城。
车到车田庄时,雨还在下,宣委的小车早已等在路边。抬头,天空灰暗,羊毛似的雨雾緾在山峦上。庄北的山最高,叫北台山,亦被大团大团的雾气裹着,山峰隐隐现现,神秘莫测。大巴跟着小车,拐进村庄,往民房穿插,只为带我们一睹千年古树的芳容。整个村庄,几乎都是白磁砖、彩砖的平顶屋,模样别致的别墅。家门前的花园里,一蓬一蓬的花草,苍翠,蓊郁,安静地沐在冬雨里。冠名[铁御史千年古樟树]的红牌子,立在不远处的池塘边,红字尤其亮眼。塘边除古樟外,别无他树。树敦实稳重,神态安详,有遗世独立之范。一方枝叶,斜向池塘,形似迎客,热情,谦卑。一行人,喊着,叫着,冲大树跑过去。跑在前方的八九个人,不约而同丢开伞,张开手臂,去环抱它的腰围,因树底福神庙间隔,努力伸直的一双臂膀,终没能合拢来。
我估摸着,树高达三十来米,树冠张幅三十米,树围约八米。枝干遒劲,如巨蟒游移。枝桠向四面八方伸展,散开,繁复错杂的线条,似闪电炸裂开来。叶茂,叶密,鲜绿得泛着油光。人站树下,伸脖仰视,自觉身轻,身小,如蚂蚁。我们这群蚂蚁,屏声敛气地站在凛然的大树下,只听到雨滴滴答答,却没被雨淋着。手机拍个不停,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一种巨大的力量感,震撼得让人想落泪。在如此体已的生物面前,我一时语塞,只觉得有把擎天立地的大伞,把我们严严实实地护着。不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了,我努力搜括脑海里的词,感觉都是苍白的,心仿佛被点化了,唯有默默注视,像仰望慈眉善目的大佛,任脉搏里血液奔流,任感动把心填满。
一群白鹅,背对大树,蹲在池塘边,齐齐望向对岸,竟没有回头看我们一眼。豆大的雨点里,它们镇定自若,旁若无人。雨和我们这群人的动静,始终没有惊扰它们。寻常的鹅,见了生人大抵会扯开喉咙嘶喊大叫,躁动不安的。随即有人就叹,古树村的鹅,格局到底不同。我把这理解为,它们见多了这种场面,人对古树的崇拜和仰视,白鹅已熟悉到骨头里了。它们的世界,风雨不侵,就像这樟树,纵然穿越千年烟雨,自泰然处之,一个劲地蓬勃,旺盛,生生不息。所以,树活成了车田一道风景,活成了车田人心中的“神”。民间传说,树是宋神宗熙宁年间,本村名士“吴三贵”栽植。吴三贵即吴中复三兄弟,均中进士,分别官拜四川督抚、京畿转运使、户部副史等职。有志之人,无论走多远,情系故土,守望家园的心,一直在的,就像这树,沉静,安然,稳如大山。此处原先有路直通北台山的,因村庄扩建,铺柏油路,拉电网而斩断。
来不及整理对树的满腔情绪,我们又坐上大巴前往北台寺。寺院静立在北台山腰,题寺额“北台寺”。门前古树参天,甘泉破石而出,鱼群在泉池里忽聚忽散。每一条鱼都是壮壮的,欢欢的。好山滋着,好水养着,它们快要成精了。黄墙黛瓦的建筑,殿宇辉煌,佛香袅袅,佛陀法相慈严。因乱寇肆虐,北台寺自明朝兴建起,屡毁屡建。到康熙丙子年,王德尚为“上继先贤乐育之志,下启后学进修之勤”,率众捐资建成。后来,又修建了以吴中复官名为号的“龙图书院”。两处建筑,是洪港祖辈“爱国、弘教、育人”之地。可惜书院已煙灭在历史的烟尘中,再无复建,遗址处唯作协文友新树一块碑,镌刻着经历的美好与磨难,以作纪念。在北台寺,我们遇见一妇人,低眉敛目,跪伏佛前。她心中的结一定对佛说了。佛是最好的听众。
雨天路滑,车无法往山势陡峭的北台山高处爬。远望,山路如网交织。路从山岔一侧上去,又从另一山的腰间盘出,一直绕到雾里。想起几年前,我同友登上北台山云凤山庄民宿区俯瞰,顿生“一览众山小”之感。身下沟壑幽深,绿草坡觅食的牛羊,细小得能纳入掌心。油茶花漫山遍野,似雪漫枝头,晶莹璀璨,像万点波光闪烁在碧海间,风情万种。更远的山,长长的绿带子般飘拂,绵延起伏,美不胜收。那天,我们离顶峰仅一步之遥,恐高的同伴,乘车上山时还虚汗满头,面如土色的。要下山那会,他竟趴在崖边的护栏上,面对北台山的旖旎风光,不肯离去。
我们在北台寺,只稍作停留。大巴回到省道上。路通畅,顺达,哪里都是好山伴着,清洌洌的泉水牵着,九曲十弯,一个劲地跑在大巴前头。到江源村已近中午时分,青砖黛瓦的屋顶上,炊烟如线,渺渺茫茫,整个村庄便弥漫着传统村落特有的气息。下车,走在村湾小道上,像童年回归。一家正宰年猪,两家磨豆腐,厨房里灶火烧得旺旺的,在炸豆腐。敌不住香味的诱惑了,有人口水直淌,端不住了,竟直走进去,做了不速之客。女主人用笑迎着,站起身来,擦手,递过炸好的豆腐让我们尝。客主两方,竟没有一点疏离感。美味在舌上打转,满口绕着黄豆的清新,菜油的香,山泉的甜。不好意思再打搅,走人,一个说,喜欢就再吃点,不要紧的。一个说,不要了,又忍不住接过她执意递来的心意。有同伴说,他老家也有江源庄这种老屋,只是没有“迪德堂”“槐轩”如此气派的八字门楼。真正走进去,喜上眉梢,吉祥如意的气息扑面而来,门墩、柱础、格窗上,精雕细琢着花鸟鱼兽,让人眼花缭乱。迪德堂建于清光绪年间,庭院一进五重,内室宽敞,牌匾高挂,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。庭堂上方,保留完好的牌匾有八块之多,每一块都古朴朴的,很久远的样子,或嘉奖忠君爱国的谋士,或旌表孝义节悌的平民,这些都是江源淳朴的民风和深厚的人文的有力见证。我真的好想上去,读一读里面的故事,抚一抚,摸一摸前人的温度。回到车田,一行人带着虔诚和好奇,又走进了王氏老屋群。同样的,门庭高阔,匾额高悬,气势庄严。我确信,但凡老屋里的物件,一块匾,一块砖,一片瓦,甚至一处绿苔,都是有故事的。这些故事,沉积在岁月的长河中,涛声依旧,情意悠悠。出王氏老屋,檐边又见,一蓬一蓬的月季,怒放着。
中饭定在洪港镇一家餐馆。馆舍在并不热闹的街道里,但装修讲究,干净整洁。喝的是本地陈年佳酿,吃的是本地传统菜肴。宣委的脸上,一直飞着笑,他说,大家放心,这些食材是纯天然的,绿色养殖的,是洪港人自家养的,亲手种的。他的语气里透着的诚恳与热情,像满地的阳光,是寒冬里心头一缕温暖。
一天的行程,张弛有度。饭后在洪港镇中心逗留片刻。街道人头攒动,秩序井然,商业气息浓郁。贾家源是我们此行最后一站,处于洪港镇东边缘地带,真真的湖北东大门,与江西接壤。站在“湖北欢迎你”的界门下,我们用心体味着,一个个抬起脚,感受一脚伸进江西,一脚留在湖北的滋味。原来,一脚踏两省,是如此的轻而易举,又意味深长。虽是两省边界,却没人把守,两边土地与房屋没有任何地方差异。新式的楼房,门前长着月季,红黄粉白,像一群妙龄女孩,挨挤一起,打闹嬉戏,美得让人惊慌失措。牛高马大的重型卡车,满载货物,一辆接一辆。它们鸣着长笛,呼啸而来,绝尘而去。我们走得很慢,一边在花世界里倾心倾肺,一边在大车的狂野中心惊肉跳。而长期工作生活在贾家源的几位向导,一直耐心等待我们,淡定地看着这一切。在他们眼里,迎来送往,花儿葱茏是如此的习以为常。
一路走来,我所见的村落,古树,工厂,房屋,以及充满生机的田野,让我感觉洪港这块风水宝地,人们的幸福生活像花儿冉冉地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