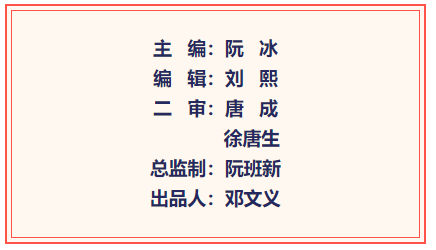红薯
作者: 陈华国
日月流转,季节轮回。深秋时节,我想起故乡的红薯。
鸡啼三遍,母亲起身,在火炉上生火,将洗净的红薯放入锣罐中,加水、加火,不时用筷子轻拭,期盼着那甜蜜的熟透。红薯蒸熟,果肉甜软,轻轻一咬便化作满口的香甜,粘粘的质感让人回味无穷,香气与热气交织,清香扑鼻而来。
时令谷雨,土地被松开、整平,底部铺上一层厚厚的肥料,薯种被小心翼翼地埋入土中,一排排、一厢厢,宛如希望的田野。覆盖上一层松土,不久,嫩芽破土而出,沐浴着春光,迎着暖风,茁壮成长。栽薯虽苦,但在雨水的滋润下,却孕育着丰收的喜悦。母亲抽空剪下薯秧,用谷草扎成小把,父亲顶风冒雨,与社员一起将薯秧插入翻松的薯地中。
薯秧生根发芽,短短的秧苗很快长成长长的薯藤,交错缠绕,满地都是。夏天一到,满眼碧绿如翡翠,蓬蓬勃勃。红薯叶的形状、大小和颜色都与绿萝相似,风一吹,绿叶波浪翻滚,似乎在诉说着夏天的故事。施肥,锄草,身姿低伏在地上,果实深埋在地下,不经意间从薯蔸里裂出缝来,犹抱琵琶半掩面,依偎在土壤里,忙着凝粉,忙着长个,似乎地里都是吮不尽的甘露,意犹未尽。就算被迫刨出,周身还粘着土粒,一副长梦未醒的样子。
秋收时节,野猪往往夜间出来抢食,边远的、大片的薯地搭建野猪棚,派人驻守。野猪虽然惹人讨嫌,终究还是怕人,一旦碰到人影、呼叫和响动就拼命逃蹿。静谧的夜晚,墨绿发亮的红薯仿佛进入梦乡,一片沉寂。山林绿叶在微风吹拂下发出籁籁的响声。秋虫的唧唧叫声从四面八方涌起,如一支动听的催眠夜曲,让大地和万物进入梦境。父亲兴致来了,跟我讲讲故事,讲完了拿着烟筒吸会儿烟,到地边转转。奇妙的夜景、秋虫的鸣唱、禾香混和的青草气息,都让人心旷神怡。
寒露刚过,红薯从土层下被唤醒,红润的身躯水灵灵的,掐一下,白色的汁浆汩汩流出。伴随着农时的节拍,沉甸甸的收获用厚实的肩膀一趟又一趟地搬回。至霜降,红薯畏寒,身现疮斑,昔日风采渐褪,失去往日的飒爽,被小心地放入薯窖中。方形窖口,木板封顶,木梯通达,世代传承,未量其容,只知岁月悠悠,一蒌蒌吊下储存,又吊上食用,一直吃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。
遗传的薯粉钵,粗口细底,釉色温润,外表质朴,内壁却如磨齿,密布沟槽。大冬天,雪雨淋淋,冷风呼呼,父亲依然坐在井边磨薯粉。左手撑住薯钵,右手握住红薯顺时针快速而节奏地旋转,日复一日,夜以继夜,薯钵上密密麻麻的齿轮磨破手指,满布裂纹。粉浆放在大型竹筛上搅拌、过滤、稀释,最终沉淀出润白如羊脂的淀粉。淀粉紧紧抱在一起,像是焊在木桶里,在太阳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
筛余薯渣,揉团发酵,晒干混煮猪食,灾年更显珍贵,薯渣粑、薯渣糊充饥,甚至酿酒,虽味苦涩,却饮之不乐乎。
贵客临门,佳节庆典,薯粉包坨不可或缺。油干、白萝卜或竹笋,猪肉切粒,葱蒜、酱油、味精调和,炒至半生。薯粉以开水浸透、搅拌、揉和,捏成坨皮,包裹馅料。锣罐加水,火炉加热,待水沸腾,包坨入锅,盖紧待熟。红薯丰收之年,薯粉富足,更可制薯粉线,打芡、勾兑、揉和,白丝顺漏瓢而下,晾干入筐,待客佳品。
岁月匆匆,故乡已人去楼空,一片荒芜。废墟上的薯窖依旧张开洞口,对着天空、对着阳光在呻吟,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热闹和辉煌。